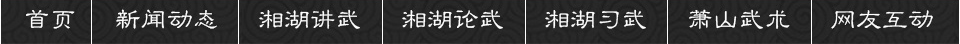中国武术是一门“向善”的学问
更新时间:2015年9月21日 21:11 内容来源:萧山网
王岗 满现维
(武汉体育学院武术学院;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在以“善”引领“真”和“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成为最重要的特质和核心价值。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以“真善美”的视角对中国武术进行解读,得出中国武术形成发展的历程既是一路向善的历程,中国武术就是不断扬善,不断向善的文化系统。在“善”的引领下,求真的武术技术出现对技击的超越,作为工具理性的武术技术变得明晰;道德的介入使由“打”而来的中国武术形成“不打”的道德要求;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高超的技艺使武术得以自由的发展,武术之美因技术与道德的整合而成为向善的学问。
关键词:中国武术 真 善 美
真善美是人们共同的“人间理想”,“是文明社会的三大特点”(周海中),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精神追求。众所周知,古今中外,求真、求善、求美一直是人们的心灵向往。大量的文献记载,从古自今中西文化一直没有间断对“真、善、美”的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偏向于兼善兼美,孔子的“尽善尽美”、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即善的就是美的;西方文化则偏向于求真求美,亚里斯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即真的就是美的。从“中华美学偏于伦理学,侧重于‘美’‘善’统一;西方美学偏重于哲学认识论,侧重于‘美’‘真’统一” [1]的文化差异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善”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质和核心价值,这一核心价值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润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中国武术,也是在这样一个核心价值的引领下,形成了一整套“扬善”的文化系统,构筑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中国武术就是在“善”的引领下所形成的一门“善学”,并且这一“善学”在当代仍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感召力。
1. “真”“善”“美”是中华民族始终不一的民族追求和个体实现的目标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求真、向善、爱美是人类的天性,是引导人们不断进步,乐观前行的驱动力量。而将伦理、道德作为核心价值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则从未停止过对“善”的追求,《礼记?大学》开篇便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是中国思想家“究天人之际”的根本目的。“西方文化讲真、善、美,注重其分辨与对照;中国文化讲真、善、美,注重其整合与统一。”[2]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的核心追求下,“真善美”被统一到“善”之中,成为一切文化活动的导向标。
“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美在某种意义上说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即“善”既是“美”。从字源上来看,“美”,《说文解字》讲“羊大为美”、“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说文解字?羊部》)另一种解释则是“人羊为美”,即人头上戴着羊首或羊角。李泽厚先生在《美学四讲》中认为:人带着羊头跳舞才是“美”的起源,“美”字与“巫”字、“舞”字最早是同一个字。这说明,“美”与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有关,具有某种社会含义在内。[3]“善”则与恶相对,《说文解字?言部》载:“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义、美同意。”
孔子讲:“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这里孔子将美与恶、君子与小人相对立,可以发现美和善在孔子的思想中是相同的,有许多的共通之处。孔子所追求的人格境界是一种高规格的道德理想,是“君子”之道。何为“君子”?孔子给出解释:“君子道有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仁、信、勇”也被儒家称为三达德,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礼记?聘礼》)“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辩,君子无不仁也。” “仁德”便是“君子”与“小人”的分别。然而,怀有“仁”心者皆可成为君子,“仁者”便是君子。“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把其提高到了道德的最高范畴,怀有“仁爱”之德,便是向善的基础,“仁者爱人”是儒家的最高追求,也是最高的“善”。清朝的戴震在《原善》中指出:“善:曰仁,曰礼,曰义,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又有“是故谓之天德者三:曰仁,曰礼,曰义,善之大目也,行之所节中也。”“善,德之建也。”(《国语?晋语》)可见“善”便是仁爱之德。基于以“仁”为基点的审美思想,孔子对美学思想的构建同样与善一样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孔子对美的论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可见,孔子所追求的就是“尽善尽美”。“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尽善’就是要使‘乐’所表现的内容没有任何不符合善的东西,‘尽美’就是要把善表现在能引起人们最大审美愉悦的感性形式中。”[4]美不应仅仅是感官上的愉悦,而且应该起到教化人们德行,使人向善的作用。孔子所讲的“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其实也就是讲的“五善”。
中国传统美学精神认为,美是在使人感官愉悦的同时使人向善,而美和善的表现则应该符合真的精神要求。
“孔子的仁不仅仅是美善的合一,而且还是真的合一。”[5]“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孔子讲究质朴,注重实际,这里讲“仁”的反面,人与人的交往应该真诚,实事求是。所以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古人质实,不尚智巧,言论未详,事实先著。”(宋?陆九渊《与朱元晦书》)人们推崇的是言行一致,先做后说的务实态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学”文化贯彻的是“文质兼修”的标准,即“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论述了文化教养和朴实本性的关系,一个人具有朴实的道德品质,但是没有文化的教养就会显露粗野,然而仅具有幽美的辞藻雕琢,掩盖了内心的本质,只会陷于浮华甚至虚伪。所以“文”和“质”必须相一致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美”和“真”必须相统一才能达到善。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以善来诠释美的,从孔子的“谓《武》,尽善矣。未尽美矣”到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可以看出二人对善与美的不同定位。但是善与美却一直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事物只有道德上符合我们的“善”的价值观念,才有可能是美的。即“美的实践就是善的表达,是对真的价值的认识。只要是真的善的就一定是美的。美是为善服务,美从属于‘仁’德。”[6]
中国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结果,并跟中国文化整体具有同源同构的‘全息映照’关系,包含有中国文化的全部‘文化基因’”[7]自然也讲究真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在“向善”的传统道德引领下,使武术技术求真,道德扬善,套路求美,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2. 从混沌到自由:中国武术的向善历程
正如“李慎之先生认为,西方学问大体上可称为求真之学,中国学问大体上可称为求善之学。”[8]作为一种自然状态的生存手段——搏斗之术,存在于中国文化环境中,自然符合中国文化的追求方向,也会不断求善、向善,最终衍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中国武术。
中国武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格斗技击之术,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下,在历史的推动下,表现为,武术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多样,文化思想越来越深刻,道德越来越丰富,行为表现越来越文明,价值功能越来越多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这种向善的趋势是武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追求的结果。
理性是人类特有的精神,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首先依据以科学范畴所具有的可量化与可预测的理性的计算手段和以人文范畴具有的对人的意义与最终归宿的价值观念,将人的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即技术的,是人们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其“特性是关心手段的适用性与有效性,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运用手段的价值取向观念。”[9]是求“真”;而价值理念即道德的,是人们对生存意义的认识,“是通过调动自身的理想自我,实现对人本质的导向作用。”[10]是求“善”。工具理性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但是任何事物都要讲求“度”,只有适度才能创造永久的价值,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对利益的过度追求,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这时价值理性就起到了对工具理性的校正,因为价值理性是“人们自身本质的导向” [11],指向的是“应做什么”,是以道德价值为主导,不以实现与结果做标准的。
作为一种以人为主体的文化,其必定要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通向自由。武术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一种向善的学问,是技术与道德的整合。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存在到有序的历程,最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摄下成为了一种道德教化,使本来是一个诡诈的小人之术成为一种君子之道。
2.1 从无序到有法:求真的武术技术因对工具理性的追求而出现对技击的超越
技术的目的是求“利”,武术最原始状态下的“利”就是技击效率的最大化,在搏斗时保证自己安全,并运用某种手段最短时间、最有效的杀伤敌人。在这种“利”的驱使下,格斗技击技术便从无的状态下慢慢的产生,并不断的发展,逐渐精炼,最终形成了对技击的超越。
武术源于古代狩猎和战争,是搏斗技术与经验的总结。远古时代人民生活在“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环境中,这种条件下“封豨、修蛇皆为民害。”人民只能通过与野兽搏斗来维持生存,进而产生了一些徒手或利用工具进行的一些搏杀手段。而人与人之间的搏斗表现在为了食物、领地等进行的争夺,这则更进一步促进了武术的产生。然而,此时搏斗的手段尚完全处于竞争的本能。有搏斗中就会有胜负之分,并会获得或失去利益(食物、领地甚至生命等),人类作为具有意识的生物,为了得到利益避免失败,便会自觉的对搏斗进行反思,将需要的生存技能进行提取,并传承下去。那么这种搏杀手段自然会不断的发展。顾拜旦说,人类具有“攻击性”和“活动性”两种本能。搏杀技能无疑是最具有满足这两种本能的原始方式。因此,原始的本能的搏杀便逐渐的成为有意而为之的技击之术。
这里技击之术的形成,不仅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而成为世界各个民族共同具有的生存本能技术。但我们不能将技击术等同于中国武术。因为作为一种生存手段,一种社会现象,技击是不受地域、民族等条件限制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掌握一定的技击手段、方法,他们的技击技术的产生也同样是对搏斗实践与经验的总结,其技击的方法在追求搏斗效率、寻求“利”的最大化方面,与中国武术此时的技击之术几乎没有差别。
但中国武术在对技击经验的总结与积累中,却逐渐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正是中国文化、中国思维与审美程式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元素融入了技击这个原初的大概念中才得以满足形成中国武术技击的条件。”[12]我们从技术表象中可以看到这一特点,中国武术的基本技法就包括:“四击”、“八法”、“十二型”,中国武术的门派之众多、技术体系之丰富是世界上任何武技都无法比拟的。在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下,武术则具有了其它武技没有出现的特殊的表象,武术的套路演练、武术特殊的练习功法、武术与中医结合对穴位的运用,以及对技击招法的以此“破”彼的思考,并且在地域性、技术的私有性等条件下形成的众多门派与拳种,都标榜了武术与其它武技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武术中招法的精炼、对器械运用的娴熟与多样,甚至以及幻想出的隔空击物、刀枪不入、飞檐走壁等高超技艺,都是在工具理性的思想下对技术的永恒追求。而“武术的唯一性恰恰在于中华民族对技击的认识与解答方式的独特性,因技击而形成的武术是对技击的超越,这种超越正如庖丁解牛中所获得的启示一样。”[13]这时的武术技术已经不再仅仅是停留在杀人、搏斗的单一的血腥功利上面了,此时对技术“功利”的追求已经变得更广泛了。
正是因为有中国文化、中国思维及审美程式的介入使武术技术这一客观表象变得明晰,成就了技击技术与中国武术形成的“缘”。
2.2 从“强战”到“不战”:求善的武术道德因价值理性而成为教化的手段
从发生学来看,一个事物从一种状态发展到另一种状态,是因为思想观念的发生。中国武术首先是一个客观的人文实体,是一个可闻、可触的文化现象,武术的技击技术就是其最初的状态,人们感知的最自然的表象就是最初的带有搏斗、攻防特征的身体活动。然而中国武术却是一个“性”“命”双修的学问,唯技术论、技术的绝对化只会导致技术的异化。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技击之术的破坏性,它表现出的残酷、冷血、无情使人们不寒而栗,不加控制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倒退,也无法获得及达到技术上的更高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加入使武术在工具理性之上获得了道德上的指导,传统道德的融入与整合是武术形成的根本动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注重一个人的德行,“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是修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国家兴亡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泛道德意识,一切活动都被道德意识所涵盖,在道德意识支配下,人们的活动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向善。这种道德意识引导的向善在武术和兵学中表现为“不战比战更重要”的价值思想,作为天下第一兵书的《孙子兵法》中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中国武术同样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由此而来的演武、说招、功力展示等武术较技方式便最有力的说明了并不是非要交手较狠才能分出高低胜负,此外对于战胜敌人来说我们还可以选择更好的办法,那就是道德感化。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 ?季氏》),而武术中讲的“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同样表明习武者对“德”的看重。人们尊重的、崇拜的习武之人,不会是仅仅武艺高超,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唯结果论者,而肯定是德高望重,德艺双修的真正武者,这点我们不论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还是在传统的拜师择人时对师傅与徒弟的双向考察中都可以看到。“因为人们习练武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在技术这个层面上。如果没有道德规范与成就人格的前提保证,所谓的武术,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武术。”[13]正如国际武术巨星李连杰所说“这几年我常常在心里谴责自己,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青少年一看到我,立刻就会摆出一副格斗的架势,打打打,蹦蹦蹦。我觉得是我误导了他们对中国武术的理解。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如同一颗大树,技击只大树的一个分枝、一个表层。武术还有另一面,就是关爱。”[14]“爱”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等无不对武术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使的武术道德成为武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使得作为一个处处体现技击的武术,却无时无刻不在讲如何“不战”,看似矛盾的表现与宣扬,实则体现了中国武术道德的“向善”心理。
事实上这种“向善”的价值取向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并对武术产生影响了。从孔子的“仁爱”到墨子的“兼爱”、“非攻”武艺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墨子学儒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继承了孔子的理想人格,但是作为儒家的第一个反对者,墨家是一个真正的武士,司马迁对“侠”赞誉为“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墨家反对一切不义的战争,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墨子为阻止两国战争常奔波游说,并且会主动担任起弱国的军事防御职责。在《墨子?公输》记载的一则故事很有意思,说公输班为楚国制军事工具,将要造攻打宋国,墨子便走了十天十夜到达楚国,游说公输班和楚王不要制造战争造成百姓伤亡。然而虽已被墨子的话所服,但楚王却说云梯已经造好了,必须攻打宋国。“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墨子看出公输班的想法,告诉楚王已经派遣弟子在宋守城,即使杀了自己也打不下宋国。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这则故事表现了墨子的非攻思想、辩论能力及守城方法。而其和公输班的对阵与武术比武式的说招、拆招是一致的,这很有意思。墨家思想对武术见义勇为、重义轻利的道德品质具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在诸子百家的思想里都在对道德进行阐述,但“作为意义存在的‘德’与作为表象存在的武的统一,却集中体现在墨侠身上”[15],其以“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判断一切价值的标准,也使得武术成为行侠仗义、为民除害等道义的实践手段。然而因墨家带有的理想主义色彩使其在秦汉以后从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地位衰落,在“独尊儒术”之后便失去了思想的主导地位,但其侠义精神与独立的人格被武术者继承了下来。儒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其作为政治工具,具有维护伦理秩序的作用。武术在儒家“仁”“义”的感召下,逐渐变为一种人文教化,从孔子将“射”作为一种礼仪教化的手段与方式,我们就能感受到在儒家思想无处不在的对人的终极目的关怀。使得武术成为具有培养人的自由意志的功能和手段,使武术有别于灌溉式的教育成为一种习染式的教化。“武术教化是以感性的身体运动形式‘动荡其血脉,固束其筋骸’,从而在一种‘涵泳从容,忽不自如’的过程中是习武者养得至善的德性。”[16]
由“打”而来的中国武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形成对“不打”的道德追求。从苌家拳的《初学条目》规定“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式正人君子。学拳宜以涵养为体,举动间要心平气和,善气迎人。学拳宜做正大事情,不可持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 以及《昆吾剑箴言》在传人方面要求“人品不端者不传;不忠不孝者不传;人无恒心者不传;不知珍重者不传;文武不就者不传;借此求财者不传;俗气入股者不传;市井刁滑者不传;骨质柔钝者不传;拳脚把势行不传”。精武体育会有“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会训和“精武十式”的行为规范,等等。体现了武术对习武者道德的教化作用。“中国武术在传统文化的牵引和道德规范的主宰下,在不自觉中走向了从本质上有别于‘原始’武技的发展界域。”[17]“武术技击不仅不与传统的伦理政治相对抗,而且自觉地充当了古代道德教化的急先锋。”[18]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和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是武术产生的“因”。
2.3 从“技术”到“人格”:武术之美因技术与道德的整合而成为向善的学问
“德性规定了能力的价值方向,能力则赋予德性以现实力量。德性与能力统一,表现为自由人格。”[19]中国武术就是通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高超的技术造诣得以自由的发展,并同时也获得自由的人格。
中国文化对社会控制方式的侧重不同于西方,在对以道德机制和法规机制的选择上,中国更倾向内在的道德控制机制,而西方更多的表现在外在法律法规的运用。这种差别导致了西方出现了标准化的竞技体育而中国则为自由的中国武术。比较中国武术和西方的竞技体育就会发现这明显的区别,在技击之术上,西方文化注重的是外在直接体验,表现为对规则的绝对尊重与利用,利用规则的强制性,保证技击术的使用尺度;而中国文化则是注重内在感悟,以道德教化人们,引导人们自觉的向符合人们价值观念的、向善的方向进取。中国武术不同于西方的拳击格斗之术,西方的格斗技术注重力量的大小,讲求以ko取胜,人们欣赏血腥的,看起来更为真实的暴力场景;中国武术则讲求“四两拨千斤”的技术,点到为止的仁义,说招拆招的君子风度,欣赏的是较技不较力的武术拳学。
以向善的道德为价值引导使得武术技术自由的发展。传统武术通过对人的道德思想引导,而不是像西方竞技体育那样对技术使用的限制和竞技规则的制定,使得武术技术的发展更为多元化。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潜在的向善心理的影射,在比武较技时,比的就不仅仅是拳脚功夫更是在拳脚相加时所表现出的仁义、慈悲,这无疑促进了各个门派对武术技术的钻研,道德的介入使武术表现的更为仁慈,但却并没有使技击丧失,反而促进了其技术的进步,技术更为丰富,如《罗汉行功短打?序言》写到点穴的创立“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即不得不打,仍示之以打而非打不可之打,而分筋截脉之道(即点穴)出焉。圣人之用心苦矣。夫所谓截脉者,不过截其血脉,壅其气息,使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短打之妙,至此极矣。有志者细心学之,方不负圣人一片婆心也”[20]点穴、擒拿甚至摔法等技术虽然同样可以致伤致残对手,但相比之下却更为不易,这些技术更容易实现的是制服对手的功用。这里可以看出东西方在道德指导和规则限制下对技击价值的不同追求,西方是在规则的限制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即不违反规则制度的情况下给予对手最严重的伤害;中国武术则是在无规则限制下将伤害降到最低程度。武术习练者在与人较技时特别注重自己的口德和手德,正如李经梧先生当年告诫弟子一样,“像‘挤劲’这类劲,能打散别人的内气,很可能会伤及对方内脏,除非万不得已不准使用。李经梧先生在于人搭手中,在对方即将跌出时及时收手,并在后来对学生说:‘对方明白就行了,不要再让人难堪,别人学到这个程度也不容易。’”“推手较技‘不一定要把对方打倒打伤。把对方拿起来放下就得了,着是练武的最高境界。弄伤了对方,自己的人格就没了。’”[21]从李经梧先生的事迹和教诲中可以体会到武术“仁义”的价值取向。高尚的武术道德促进了武术技术的提高,高超的武术技术表达着高尚的武术人格,即武术的“美”的精神通过“美”的技术而表达出来。
向善的道德引导同时使武术的价值得以自由的表现。武术道德使较狠、尚力的技击技术成为一个表达仁爱,诉说人格的中国武术。武术也成为多方位表现或再现技击的艺术。中国传统文化的介入使得武术被赋予了多重的价值及功能,它的出现是因为武术在道德指导下追求的技击不是再仅仅为了技击,那么由技击而来的武术便有了更多的价值取向。武术成为了修身养性、休闲娱乐、养生悟道、防身自卫等多重的功能与价值的文化体系。武术的本质特征和活动方式表明它可以防身自卫,可以修身健身,另外武术也可以进行表演,可以很自然的融入到戏曲、电影等艺术形式当中去,相比其他武技却很少有能如此彻底、如此自然的表现出其他功能和融入到其他艺术当中。这不得不归功与传统道德对武术的去暴力化。去暴力化使武术套路成为武术主要的存在方式,也成为有别于域外武技的最具特色的内容及表现形式。
套路的出现是中国武术对中国文化的综合体现,是武术最高境界的“美”的表现形式。中国文化充满了自觉的审美意识,“西方有把艺术技术化的倾向,中国则有把技术艺术化的倾向”武术套路便是格斗技术的升华,是格斗技术的去暴力化、去血腥化的体现,“是一种融技击性、养生性、艺术性与一体的实用艺术。”[22]人们可以通过套路的习练来防身自卫,“活动手足,勤贯肢体”,并且我们通过武术套路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中国文化内在的审美情趣。武术套路来源于攻防格斗,“是人们‘琢磨’、‘推敲’,对技击术进行提炼、加工,而表现了一种战斗的‘生活’。”[23]是对战斗“生活”的艺术化处理。作为具有艺术性的武术套路来说它“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它比真实的打斗更具有典型性,更理想化。从武术套路再现的攻防的战斗图景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演练者勇往直前的无畏、舍己从人的宽容、随曲就伸的大度、避实就虚的机智、跳跃起伏的灵活、闪转腾挪的机敏等心理情感。这些美的性格足以使武术的习练者和观赏者忘却武术的暴力色彩,而沉浸在高雅的,诗意的艺术殿堂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套路与格斗有一定的联系,但并非完全是一回事,套路动作既没有脱离技击之‘真’,也没有执着格斗之‘实’,处于‘离形得似’‘不即不离’的‘似与不似之间’。”[24]“当技击与社会及个人的目的、需要完美地结合起来时,当掌握真与现实善的本质力量,通过武术这一具体而又光辉形象显示出来时,武术就进入了美的境界。”[25]武术的美是在技击术之“真”的基础上经过人们道德上对“善”的追求和融合而形成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实用艺术。
中国武术在传统文化的熏染下,由一种技击手段衍化成为一个文化体系,自觉的融合人们的养生意识和审美意识,使武术习练者可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武术价值便随着人这一主体的改变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倾向。但武术是具有综合价值的文化体系,不同的价值表现仅仅是因习练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而已,武术本身是多种文化属性兼具的,不可能只取有某一种价值而完全抛弃其他的价值,否则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武术了。
在现代,中国武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它的技击功能价值逐渐让位于教育、竞赛、健身、娱乐价值,而成为当下和未来武术的主要功能价值,这里虽然有时代变迁的社会因素使然,但应该肯定地说,它的生命长久之动力,更是因为武术所具有的“向善”的内在品格所铸就的。
3 结语
当今,提到人们对中国武术的认识,总会出现两种状态,一是武术是用来打架的手段,二是认为武术就是花拳绣腿,故弄玄虚,远不如跆拳道、柔道、泰拳等来得实在,将武术的本质特征理解为武术的唯一价值。这些无不是唯技击论的功利主义者。中国武术虽发源于技击,但在向善的价值引导下追求的是自由人格的理想。从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狭义精神,到儒家的礼仪道德教化;从以“较技不较力”为主要的价值诉求,到当今所求的健身、娱乐价值。可以说武术是一路向善,一路扬善的。武术不是技术的而是文化的,是“真善美”相统一的文化体系,既有技术的真,又有道德的善,还有艺术的美。我们应该“挖掘武术文化的优秀因子,张扬‘和谐’,倡导‘为善’,抵拒‘暴力’,追求‘艺术’,以架构和推崇一种满足未来世界和谐发展的文化为己任,树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担负美好‘国家形象’的文化使命。”[ ]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何为武术的本真,使武术在当代社会成为一个道德教化,使人向善的修为方式。通过武术的习练让人们在经济至上的功利主义中找回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人活在这世上,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完善。适者生存,善者优存,善者乐存,心有真善美的追求,才有完美的人生” 的生命意义。
故此,我们认为:中国武术作为一门善学,在当代对于社会个体而言,应该具有这样的价值和功能。
1. 王离湘.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艺术创作的基本遵循[N]. 中国文化报,2015-07-10003.
2. 单纯. “真善美”探源[J]. 浙江社会科学,1999,06:120-128.
3. 转引李泽厚.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01:249
4. 刘纲纪. 成于“尽善尽美”[N]. 人民日报,2015-07-10024.
5. 何璐. 孔子论美[J]. 赤子(上中旬),2015,14:99.
6. 张世英. “东方睡狮”自我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之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5:5-13.
7.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 中国武术史[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1.
8. 单纯. “真善美”探源[J]. 浙江社会科学,1999,06:120-128.
9. 苗春凤. 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J].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12:15-16+18
10. 魏小兰. 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J].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4,02:63-67.
11. 魏小兰. 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J].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4,02:63-67.
12. 王岗. 中国武术文化要义[M],山西: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09: 06
13. 张江华,刘定一. 起点即终点:武术发展的知识向度[J]. 体育科学,2012,05:42-48.
14. 乔凤杰. 本然与超然——论传统武术技击的诡道与圣道(二)[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5,03:10-14.
15. 罗京生. 李连杰:当形象大使只为做慈善[N].光明日报,2007-11-14,06
16. 张震,张长念. 传统社会中武术的异化及其现代性复归[J]. 体育科学,2015,05:88-95.
17. 王岗. 中国武术文化要义[M].山西: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09: 231,146
18. 乔凤杰. 本然与超然——论传统武术技击的诡道与圣道(一)[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5,02:14-17.
19. 杨国荣. 再思儒学:回归“仁”与“礼”的统一[N]. 文汇报,2015-07-31T07
20. 转引程大力. 武德仁学中心论[J]. 体育文史,1990,03:56-61.
21. 梅墨生. 大道显隐:李经梧太极人生[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9:27,180
22. 乔凤杰. 文化符号:武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112
23. 邱丕相. 中国武术文化散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232
24. 邱丕相. 武术初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7:32
25. 赵燕,彭鹏,曾天雪. 论武术中的真善美[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01:154-155.
26. 王 岗. “中国制造”、“中国形象”与中国武术[J]. 搏击(武术科学),2010,01:2.
作者: 编辑:姚晨曦